福建古田县岭尾村:“金翼”之家60年变迁
|
“四哥”从抗战以来渐渐发迹,他利用苛刻的租佃与私人借贷方式沉溺于扩张土地,却丝毫没有预感到脚下已孕育着的烈焰。
第二天,林耀华陪同四哥去谷口镇拜访了区委的领导,但此次返乡之行并没有对改变四哥命运起到什么作用。1951年1月5日,在小哥离开家乡半年之后,一支土地改革工作队进了村。 根据当时当地地主每户所有土地的平均数量衡量,以及解放前3年的时间量比较,四哥的土地已大大超过划为地主的规定,时限又刚好在40年代的最后5年中。几次斗争会之后,阶级成分张榜公布,金翼之家被定为“地主”,而四哥则是地主中的“恶霸地主”被人民法庭押走。 不久,一个消息传到了村庄,四哥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消息传来,金翼之家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他本可以不死的,可工作组说有人命案,实际上是村里有个人死了,我父亲好心给他买了棺木,就被安插了这个罪名。”时过近60年,林荣昌说起父亲之死仍耿耿于怀。 但1986年林耀华的学生庄孔韶回访村里老人时记录下的却是另一番见解。当年60多岁的老人黄学友(化名)说:“被占了田的农人揭发他,连同宗的人也指责他,谷口镇的少扬是个老实人,在店里总受气,所以在解放之初,少扬妻一点也不饶他,揭他的老底,向他索还田地的人都成了控诉地主大会的积极分子。” 中国乡里社会具有强大的宗族势力,原本念在同宗的情分,即使控诉也不会太过分,但让四哥失望的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了。 “当时土改政策定了成分,乡民们唯恐表现不积极,有句话就叫‘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向地主阶级来一个大进军’。”村里老人回忆道。 宗族、家族内外的利益恩怨之争在遇到阶级战线时已混为一谈,它最终没有改变四哥的命运。 “银翅”展开 1970年前后,“文化大革命”中的城市还在闹腾,在闽江流域的村庄,农民已经厌倦了暴风骤雨的运动,饿着肚子的农民四处寻找着机会。 林荣昌的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一天天长大了,他面临的苦恼是,仄逼的房子如何容纳这么多口人,他和几个儿子到山上砍伐杉木想盖房子,但因为“地主”成分,盖房被村委会叫停了,最后杉木被上缴了。 在古田的女儿此时却捎来消息,说县城里有人在种一种叫银耳的东西,很好赚钱,虽然对这个新东西一无所知,但此时窘迫的林荣昌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与三个儿子决定试手一干。 关于银耳在古田县的扎根,如今听起来确实是个传奇,从一穷二白的山区县,到成为“中国食用菌之都”(古田县目前生产的银耳占了世界产量的90%,占全中国的95%),古田只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如今在古田,几乎每户家庭都对银耳的故事耳熟能详。1969年,古田县一个叫姚淑先的年轻人偶然在枫树上发现一朵7层的大银耳,周围潮湿的气候,林中的散射光,深山里的新鲜空气,形成了巨耳子实体分化的最佳条件,这让他产生了用人工创造模拟环境培育银耳的想法。但他的试验直到1977年才真正获得成功,那一次姚淑先代料栽培的5000瓶银耳大丰收,获利甚多。求教的农人纷至沓来,是按照传统秘而不宣,还是公之于众,姚淑先选择了把技术向世代务农的乡里人开放。1981年,福建省委书记项南视察了他的工厂,《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均以显著位置报道过他的故事。 代料取代原木,这个里程碑式的创举,造就了古田后来蓬勃发展的食用菌产业,70年代末,岭尾村农人也被卷入了这场食用革命。 虽然比其他家穷,但林荣昌家令人羡慕的是,他有着三个能干的儿子和四个巧干的女儿。 银耳栽培在农忙季节结束后进行,普通农家每年能种三四批,但劳动力多的林荣昌一家可以做到10批以上。“银耳有个好处,三四十天就能完成一批,我们家三兄弟一起做,第一次就赚了一千多块钱,那时在生产队赚工分,三个劳动力一天也就赚1块钱,365天就是365元,当时一下子拿到那么多钱,想想真是赚翻了!”回忆赚取第一桶金的历程,林荣昌的儿子林应芳至今仍喜得合不拢嘴。 听说外地银耳能卖好价钱,80年代初,林应芳和同乡同行第一次做坐上火车,跑起了“推销”,他们的足迹走过了福州、北京、广州、沈阳等中国多个城市。 在几十年后,族人间曾经的隔阂却因一项生计在淡去。“当时大家连福州城都没有去过,心中不免发慌,何况是大城市,”林应芳回忆道,这个30年来的第一次个体推销活动首站就是广州,聚集了三四十个同行,浩浩荡荡出行。“银耳经济”让金翼之家生活正朝着一条向上的曲线前行,林应芳说他第一次感觉到,“地主”的身份不再是扎眼的标签,他的族人已经能够接受他们了。 在80年代中期,荣昌家已经能买起一部14000元的胶轮拖拉机来运输银耳,这也是村庄里买车的最高价,这次他们得到的更是村里啧啧的赞叹声。 岭尾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起了银耳,1986年冬季,庄孔韶回访岭尾村,记下了这番令他激动的景象:“入冬的一天晚上,月明星稀,我从黄村山岗农家做客出来,站在高高的泥土路上,吸一口清凉的空气。眼望橄榄状的山谷,看到黄村农家门前、道边晾着白木耳的竹草席还未收起,上面密布的白木耳层和月光交相映照,狭长的一片又一片,像无数舒展的银色翅膀。” “昔日的金翼消失了,幸运的银翅又降落在这同一块土地上,”——— 庄孔韶在《银翅》中感性地写道。 宗族远去 沉寂了60多年后,金翼之家和外界又开始了联系,当年曾经作为一条商旅要道的“西路”,再次成为金翼之家农村生活与商业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 60年间,金翼之家所在的岭尾村大致保持原有的风貌,但其周围却发生了称得上“翻天覆地”的变化。1958年和1989年,因国家建设古田溪水电站和水口水电站,古田县库区大移民共计63000人,先后淹没一座千年古城和69个村(居),古田人两次牺牲自己的家园,成为全国少有、福建仅有的重点库区县,而这其中就包括在《金翼》小说中曾经喧嚣繁华的谷口镇。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被西路斩断龙脉的“龙吐珠”张芬洲宅地,上世纪五十年代作为库区移民搬迁点被占用,到1989年水口水库修成后,这里又被认为是地质灾害点被拆除,移民再次被分散到小村的各个角落。 如今的岭尾村已不再是林家姻亲组成的大家族单姓村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既有像林荣昌这样的本土居民,也有重建家园后的库区移民,从五十年代起,新旧居民一直和睦相处,从未发生过宗族械斗,这一点倒与南方农村近年来日益抬头的宗族势力复兴情形大为迥异。 林荣昌告诉记者,林氏唯一的一本族谱在“文革”中曾被烧毁。但他并没有要重修族谱的打算,这几年令他比较满意的是族人把村内的一座敬奉陈婧姑的庙宇重修,每年的正月初九,村民们去镇上请神,这是一年里村庄最大的节日。 林荣昌还念念不忘一件事,他的祖父亲手缔造的金翼祖屋,是否还有机会拿回来? 和长辈们不同,林荣昌的孙辈们对生计等现实的事情更有热情。林应芳的几个儿子走了一条和他不同的路子。前几年,村里有人去江西学习了做瓦罐汤的技术,在福州的一些高校开起了小档口,没想到效益不错,岭尾村不少农人便放弃了银耳生计,纷纷做起了小档口的生意。 “现在做银耳都是要有技术,小打小闹赚不了大钱。”林应芳告诉记者,村里人觉得还不如出去做生意好。 炎热的七月,山谷里吹来清爽的风,村庄路口的杂货铺居然人头涌涌。“你如果平时来肯定找不到几个人,现在放暑假,大家都回来,开学了再回去。”凤亭村的村主任林芳贤告诉记者,整个凤亭村1692人400多户,如今三分之一的人做“银耳”,三分之一的人在做“瓦罐”,还有三分之一种经济作物,像荣昌家就有四户在做瓦罐生意,“出去开店一年赚十万没问题,但散户做银耳就不能保证了。” 村里人最近还在热议的一件事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京福高铁合(肥)福(州)客运专线,已通过国家发改委的预先可行性报告,如果工程可行性报告完成的话,预计今年年底就可以动工,修建后的高铁距离古田县城仅17公里,距离岭尾村更只有4公里,可以预想它给古田乃至岭尾的村民带来的是怎样的机遇。虽然至今村里人尚无一人读过《金翼》这本书,但村民仍笃信风水,先祖开辟的这块土地给他们留下的福荫。 http://www.southcn.com/nfdaily/special/2009sp/60y/jiaguo/content/2009-09/10/content_5756813.htm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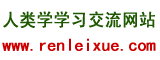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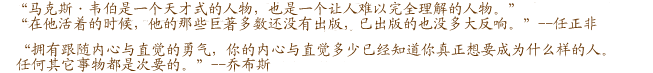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福建古田县岭尾村:“金翼”之家60年变迁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