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六章 社会
| 近的按父系继承的习俗情况下,家庭的发展本身就导致宗法统治的建立。我们可以设想,某一个家庭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建立了新的移居地,这个移居地就在父亲的统治下产生了。随着一座座新茅屋在第一座房子周围的建立,父亲就成为发展起来的氏族的领袖。但是当他老了的时候,他的长子就越来越以他的名义来行使权力;而在他死后,也就被承认继承公社的领导权。于是在这里就看到了世袭领袖或部族家长的提高过程,长子作为被赋予或大或小的实际权力的祖先代表的提高过程。但是,在这里也存在把他的继承者免职的实际可能性。如果继承者是极其懦弱,或者专横,或者愚钝的话,那么就让他的叔叔或弟弟代替他的地位,虽然在这方面的继承系统并未改变。宗法体系在整个文明世界流传很广。它不限于某种特殊的种族或民族,但是在现时,既可能在印度的黑皮肤的山民中,又可以在西非的黑人中进行研究。对我们来说,旧约《圣经》中的这种宗法体系是特别著名的;旧约《圣经》证明它在游牧民族中所采取的那种形式,它的那种变化不大的形式在按漠的阿拉伯人中还可以观察到。阿拉伯人的氏族和部族是由他们的家长、族长或首长统治的。宗法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雅利安种族的政治制度的基础;那里的这种体系的遗留,还可以在印度和俄罗斯的农村公社中去按迹探求:在这里,村长在“白发老人”的代表会上担任主席,他是以其周围的民族小支的族长为古代家长的当代代表。在这类温和的统治下,欲望还未发展的人们,在和平时期能够安乐地生活,停留在淳朴的共产主义中,这里既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这种社会的薄弱一面在于它未必能够日渐发展,、因为在那种受指导祖先的祖宗习俗统治的社会里,文明的发展中止了。在世界上,战争到处都使某种较强有力的和较合理的统治成为必需。使一帮蒙昧人的后裔成为文明民族的这种变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军事领袖们活动的结果。人类学学习交流网站http://www.renleixue.com/制作
当战争在这类非文明民族中爆发的时候,和平的统治者就退居一旁,而把统率者推到他的位子上;或者,在军事部族中,军事领袖可能是一切时期的行动首脑。当然,他是受过考验的战士,他的坚韧精神甚至能够经受住特殊的考验,例如,像在加勒比人中所做的那样,军事领袖的候选人要经受下列考验:用鞭子对他进行无情鞭打,和将他抓破,放在绿叶燃烧的火上烟熏,把他埋在蚁垤中直到腰部。在美洲,我们甚至见到考取国王称号的原则,例如,智利的部族把一个能扛起最大的树,并扛到比其余应试者都远的地方的人选为统治者。在这些粗野地区,当战争把没有联系的一群人变为一支在为了巩固纪律而被赋予生死权力的领袖统率下的军队的时候,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当自然科学家马图斯(Martius)同一位米兰哈人(Miranha)的领袖在一座巴西森林里旅行时,他们走到一棵无花果树跟前,见到一具人的骨架被蔓生植物拧成的绳子捆在它的干上。领袖忧郁地解释说,这是他的一个士兵,这士兵违抗了他请邻近部族来反抗入侵的乌马瓦人(Umauas)的命令,就被捆在这里用箭射死了。在野蛮地区,时常可以看到部族领袖和军事领袖并列,但是当有一天弓和枪的力量得以表现的时候,那么这种力量就容易得到更大发展。通过全部历史,战争使嫡亲长子成为勇敢而有才能的首领,这样的首领名义上能随着战争的停止而终止,但他却切望转到终身独裁上去。在普通民事上的军事统治,实际上就是专制主义,而且如果军事首领就这样地成为自己国家的暴君,那么在他所征服的国家里,他的统治很快就会变得更加残酷。黑人王国达荷美(两世纪野蛮人的军事统治的结果)是人民能够如此屈从于专制君主的惊人例子。人民认为专制君主像神明一样;臣民们接近君主的时候,要四肢着地爬行,同时往自己头上撒土;整个民族都是他的奴隶,他可以随意夺去他们的生命;全部妇女都属于他,他可以拿她们来馈赠,或出卖她们;整个国家都属于他,没有他的最高裁可,谁也不能占有什么。亚洲人民的国王在理论上是像达荷美的国王那样毫无限制的,但是在实际上,随着文明的发展,国王提出或批准了约束他和他的继承者的法律,使社会较为稳定而生活尚可忍受。同样,只要宗教在国家中变成一种势力,它就把普通民事的和军事的统治结合或混合起来。例如,在黑人中,司祭长和军事长官可能是两个政府首脑,而其实,秘鲁的印加人,首先作为太阳神的后裔和代表以父亲般的专制主义统治着自己的人民,为自己的臣民规定了他们必须做的事:既要吃饭,又要穿戴,还要跟人结婚。在这类国家中,国王的头衔必须是在统治者的非几家族中继承的,本质上是僧侣的政权,不论如何获得,都力求变成世袭,主要是军人的王位篡夺者按宗法领袖的样式建立了王朝。由此看来,最高政权可能是选举的、世袭的、军人的、宗教的,无论按迹探求国家的发展如何困难,在各国家中总是可以指出这些成分的某种综合的影响。 在看到了某一野蛮部族准备侵犯敌对政权或保卫自己的疆界的旅行家中,能够找到对团结那些结合松散的社会群体的作用的记述。粮食和财物拿去共同储藏,战士们屈从于首领的变换无常的意愿,局部的争吵被较为广泛的爱国感情所吞没。远方的各亲戚氏族,为了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而会合起来,而彼此没有这种天然联系的邻近部族则结为联盟,而且他们的领袖服从于由他们一起选出的一个首领。在这里我们看到,历史上最伟大事实中的具有最简单形式的两个组合:有组织的军队和部族联盟。在这种军队里,各支部队都是在一个总司令统一率领下由它们各自的长官领导。而这种联盟,就类似高级文明社会中所说的建立政治联邦,如在希腊和瑞士的情况那样。从战后继续存在的这类部族联盟中就产生了民族;同时,最强有力的部族的长官,常常就变成了联盟之王,如在古代的墨西哥就是这样。这样结合成的部族,通常是说同样语言的一个种族,因为这到处都是天然的联系。当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民族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如多利安人或海伦人,他们甘愿利用古代的宗法观念,并自以为是较亲近的,或比起他们的实际情况来是更属于一个民族(nation)或“出身”(birth)的,甚至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虚构一个民族祖先。各种事件经过了不同的发展过程,但却得到了十分相似的结果。当某一卡菲尔人的领袖,征服了周围部族,使他们屈服在自己之下,强迫战败的领袖们给他纳贡,并让战士们参加他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建立在像某位凯撒或拿破仑的帝国那样基础之上的帝国,只不过规模很小,环境粗野罢了。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各民族的早期历史上,如此极难确定一个民族在何种程度上是从一个未跟其他部族混合的部族中发展起来的,还是通过联合和征服形成的。他们的神的多种多样性,证明必定发生过这种民族的混合。直到一个部族独立地发展之前,同一部族的神的名字和宗教仪式,对于所有氏族来说都是联合的系带,甚至当迁移到远方某地去以后,他们有时也要到自己故乡的祭坛会朝拜。但是,在各民族混合起来以后,仍然还保持着它们各自的神,例如,像在秘鲁人中所发生的那样。秘鲁人把自己的伟大的神提到最高地位上以后,也给被征服的部族的神提供地位。在古代埃及,每一个地区都以各种不同的神进行组合,这一点就证明是许多小国和地方宗教组成了这个专制的国家和这个大的教阶制度。很明显,人类的高度文明是通过史前漫长时期所形成的民族特性的增长而发生的。分散的野蛮人的家庭在那范围显得十分广阔的国土上,能够在没有强有力政府的情况下生活,但是,当人们作为人口众多的民族来生活,并且形成了人口稠密的城市的时候,就必须建立社会秩序。不能怀疑,这种政治秩序是由军事秩序发展而来。战争不只授予君主对整个联盟的权力,而且他的军队也为他做出了借以组织这个民族的榜样。借助军事原则,人类学会了服从权力和遵照一个人的命令行动,这种事实是最明显的历史教训之~。埃及和巴比伦,凭借它们那不仅普及到真正的军队,而且普及到祭司和公民的所有等级的军事制度,在古代较一切国家都更加发展了工业,增大了财富,它们是文学和科学的真正奠基者。它们为未来的世纪建立了社会管理的制度,这是新时代较自由的人为了自己的幸福而自愿服从的管理。立宪的统治,它将称作共和的还是称作君主的呢?它是一种这样的结构,按照这种结构,民族借助军事专政的机构来进行自我管理。 随着部族和民族的社会变成了较为复杂的体制,社会早就已经开始分成为阶级或等级。如果我们要寻求联合代表大会的著名基本原则,“所有人一律平等”,那么,就要去找蒙昧的狩猎人和森林居民——就是在那里也远非总是如此。事实上,在哪里也未必能找得到这类平等。所有区分为自由人和奴隶中的最卓越者,从下面这个时刻起就获得了主宰权,那个时刻就是野蛮人的军队饶恕了战败的敌人的性命,把他们占为己有,强迫他们为自己工作,为自己耕种土地。在哪个低级文明阶段上开始了这类现象,可以从下面看出。被禁止携带武器的奴隶等级,组成了许多低级美洲部族的一部分。奴隶何以被公认为是古代社会的重要因素,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这种奴隶是以这样的形式讲入了希伯来人的宗法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男女奴隶在一个人的财产数目中被提到时,就像他的牛和驴一样。罗马的法律也没有什么两样,这一点,可以从family——“家庭”这个词中看出。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并不是“孩子们”,而是“奴隶们”(famulus)。我们生活在奴隶制的最后残余正在高级民族中消失的日子里。虽然文明世界发展得高于这种古代制度,但是古代社会给文明世界带来的益处,却是毫无疑义的。正是由于有了奴隶的劳动,农业和工业才扩大了,财富才积累起来了,祭司、作家、诗人、哲学家们才得到了闲暇,才得以提高人类的思维水平。大概现在雇佣工作或职务的习俗,就是从奴隶制度发展而来,其名称“仆人”(service)也来自“奴隶”(servus),这个名称本身就把伟大的社会变革史告诉了我们。领主最初是强迫奴隶为他的利益劳动;后来,自由人也发现为自己的利益而谋取工作是可以赚钱的,于是,一个巨大的靠工资生活的人的阶级就发展了起来。这个阶级的数量和影响,在新旧社会之间表现出如此鲜明的区别。在所有的社会中,除了最小的和最简单的社会以外,自由人也分等级。古诺曼人把人分为三个阶级;伯爵(earls)、自由民(churls)和奴隶(thralls)。从其粗略的特点来看,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贵族、自由人和奴隶相近似。贵族也分为不同的等级,特别是那些能够提出王族出身的要求的人,组成了公爵一等,他们瞧不起在军队、在国家机关和在教会中的首领和官员:这些人形成了贵族的最低等。 随着民族在人口、财富和智力方面的发展,统治机构应当受到改善。古老的粗野的方法不再符合目的,劳动分工的原则不得不应用到政治机关上。例如,执行审判的义务是领袖的原始义务之一。卡菲尔人领袖的专门职责,就在于解决他的臣民之间的诉讼;每一方都送给他牛做礼物。在高级文明阶段上,东方的君主坐在“司法门”旁;在古代的日耳曼人中也是这样,国王坐在王位上,宣读他亲自审判的判词。我们的审判也还仍然是国王的,但司法的实际执行早已转到专门法官的手中。同样也有由另外的管理部门来进行的。在文明上升到古代埃及和巴比伦水平的那个时期之前,社会事业是由那些像在军队中一样按等分配的官僚们管理,他们征收税捐,指挥社会工作,惩罚过失,从事人们之间的审判。刚才指出过,在新的民族中,是在多么大程度上保留了跟古代制度相似的职位制度。像我们(英国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切民族中的最自由者,但我们保留着君主专制的形式,最高权力,是通过王权公仆直到税收征集人员和警察人员来执行的。文明的统治制度的轮廓,在蒙昧人和野蛮人的政治机构中已有表现。我们看到了,在那些粗野的部族中,出现了领袖或国王,他在高级民族中也以某种形式保持着自己的地位。甚至共和国的执政官或总统,也有点像暂时选出的国王。议院也具有不少古代的特点。在美国西部大草原上,某一印第安部族的会议篝火周围蹲着的老人们,比起文明民族的上议院议员来,在自己的氏族内具有更大的影响,因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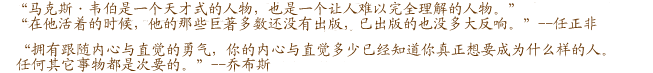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六章 社会所有评论